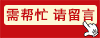殺頭潲豬等過年
很多年前,在湘南農村,種田和養豬幾乎是每家每戶的通用模式,搞“大集體”后期即已流行,土地承包經營到戶后又延續了很長一段時間,只是后來隨著外出務工人員的增多和農村建房用地的需要,荒廢的豬舍慢慢都被拆除了,特別是隨著人們對環境衛生認識水平的提高,農戶散養的現象基本絕跡,搞集中養殖的大戶倒是涌現了不少。
那個時候,家家戶戶都會養上一兩頭豬,既為了以備不時之需,譬如遇到家人有三病兩痛的、小孩讀書要用錢的,把豬賣了就能湊幾個錢、幫上一點忙。更重要的,是到了過年的時候有年豬殺,這可是臉上有光的大事,非同小可。記得父母那時候就愛念叨,有錢冒錢,殺豬過年,若是過年前沒殺豬,他們會覺得在左鄰右舍中抬不起頭的。
一般來說,農戶養豬都是每年4、5月左右買進小豬崽,喂到年底差不多就可以出欄了,是賣活豬亦或是殺豬賣肉,這就要視各家情形而定了。當然也有當年不作處理、要等到第二年開春后殺豬賣肉的人家,這樣的人家不外乎兩種情形,一是養的豬多,殺了年豬,欄舍里還有;二是特別精明,過年的時候殺豬,大家都趕趟,肉多價賤,賣不上好價錢,第二年開春后正是青黃不接之時,豬肉肯定好賣。
養豬不是一件簡單的事。圈養的家豬,只有兩項活動:吃了睡,睡了吃,對豬食的需求量特別大。那時候還沒有專門的喂豬飼料一說,曾在湖南紅極一時的“正虹”牌豬飼料也是上個世紀90年代末期的事,至于后來電視上“飼料霸屏”的局面還遠遠沒有出現。當時農戶家養豬,主要吃谷糠、青菜、酒糟之類,還有家庭里一日三餐的剩飯剩菜,這些還不夠,就得安排家人時不時外出打豬草。吃這類東西長大的豬,農村俗稱為“潲豬”,潲豬肉肥瘦適中,肉質緊實,鮮美可口,天然無公害,時至今日,仍是人們的追捧所在。
我的父母做田里的活都是好手,但養豬一事卻不是他倆的強項,一樣的喂養,一樣的操持,但三天兩頭要請獸醫過來,到年底的時候,鄰居在隔壁欄舍養的豬膘肥體壯,我家欄舍的豬明顯要小一號、小幾號。有一年,氣得父母從鄰近村請來了一個“法師”,又是焚香,又是燒紙的,末了還往欄舍里扔了幾掛鞭炮,把兩頭豬炸得嗷嗷直叫,但那年養的豬仍舊長得不咋的。
豬不長,家里人要多受不少罪。父母操勞自不用說,連帶我和姐姐也要比別人家的孩子辛苦些。那個年代,人吃的糧食尚且勉勉強強,吃剩下的自然不多,父母便在自留地上多種了一些菜,而我和姐姐的任務則是每天早上一籃豬草。
我的老家在衡東縣大浦鎮三才村,屋門前有一條叫“堰子”的小河,發源于德圳沖里,自南向北流入霞流鎮的“白衣港”后匯入湘江。橫亙小河的是一座解放前就有的小石橋,叫曾家橋,往上依次有陽門橋、黃屋橋和S336線飛躍橋,往下是平田橋和京廣線鐵路橋,從飛躍橋到鐵路橋七八公里長的河段,都是沿岸農家喂豬打草的范圍。那時候,河水清澈,水草豐滿,尤其是河里長著一種叫做“扁擔草”的水草,是打草人的最愛,叢叢簇簇,蓊郁蔥蘢,跳到水中小范圍抓扯,就可以完成大人們安排的一天任務。至于兩岸的土坡上,還生長著紫花苜蓿、苦荬菜、魚腥草、馬齒莧、灰灰菜、蒲公英等野草,都是可以用來煮熟做豬食的。
少年的我們,尋豬草的最愛線路,是順著小河往鐵路橋方向走,不僅是越往下走水面越寬、水草越多,而且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因素——可以近距離看火車。那時候京廣鐵路線上電力機車已經很普遍了,但貨運列車還大都使用蒸汽內燃機作動力,經過鐵路橋時,火車司機遠遠的就會拉響汽笛,一聲聲嗚鳴響徹云霄,鋼鐵巨獸急速駛來的壓迫感扣人心弦,伴隨車輪與鐵軌碰撞產生的“哐當哐當”聲,仿佛大地都在顫抖。列車掛載很長,幾十節車廂,人站在一個地方不動,感覺一輛列車要全部經過完,需要好幾分鐘時間,在這幾分鐘里,人會感到非常渺小,有種風馳電掣、泰山壓頂、呼吸急促的感覺。遇到綠皮火車通過,膽子大的伙伴還敢朝車窗背后的乘客做上一個鬼臉,或者是大聲吼叫幾下,并使勁揮動小手臂,以示自己的友好與勇敢。
暑往寒來,一年的辛苦忙碌,最終是看宰殺年豬。冬至一到,就進入了宰殺旺季。經常到我們組進行宰殺活動的,是本村一位姓綦的屠戶。綦屠戶中等身材,40多歲的樣子,長相英俊,談吐文雅,若不是穿在身上的一條圍兜油光發亮,根本看不出他做著“白刀子進,紅刀子出”的營生。
殺豬那天,是我們一家既緊張又幸福的時刻。大約凌晨二三鐘的時候,事先接到通知的七大姑八大姨們陸續趕了回來,大家聚在堂屋里烤著火,一邊訴說著家長里短,一邊在等候綦屠戶的到來。4點鐘左右,綦屠戶會如約而至。大家紛紛散開幫忙,掌燈的,幫忙捉豬的,燒水做飯的,照看小孩的,忙而不亂,輕車熟路。綦屠戶不慌不忙穿上他的標志性圍兜,在眾人的幫助下把拼命掙扎的“二師兄”按在用四條長凳拼做的操作臺上,對準咽喉處快速一刀,一股水柱狀的鮮紅隨即噴薄而出,直瀉到事先準備好的木盆里。之后便是“小豬變大豬”、“開水燙死豬”、“內外科手術”等環節。最讓我驚奇的是“小豬變大豬”節目,綦屠戶用刀將豬的四蹄皮肉處各挑開一個口子,用一根鐵質通條從口子插入豬體各個部位,然后對著口子使勁吹氣,不一會的功夫,豬的各處便鼓脹起來,全身找不到一處褶皺。據說,這樣做是方便后面的褪毛工序,而且肉質會更加鮮嫩。
最后是豬肉處理環節。有的年份,親朋戚友可以將一頭豬包括內臟、排骨、龍骨、豬腳等全部買走,有的年份,大家選購之后還有剩余的,父親就會請綦屠戶帶到附近集市上去賣,這樣做,家里會立馬有現金進帳,而親戚買去的,還不知道什么時候有錢付。
當然,殺年豬的當天早餐,毫無疑問是一次親朋戚友大會餐,新鮮的豬血丸子湯,嫩炒豬干,紅蘿卜燜肺片,還有干辣椒炒大腸,這幾樣都是母親的絕活。辛苦一年,一場忙碌,家里留下的不過二三斤肉和一個待處理的豬頭,而這,十有八九就是我家過年的硬菜了。
一晃,幾十年過去了,我家早已不再養豬,更不會宰殺年豬了。我問父母,那時忙忙碌碌為了什么。年近九旬的父母親頓了頓,然后字斟句酌地開口道,我們那是在過日子。我沉默了,也許,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生活,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活法,珍惜當下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