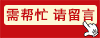方富貴丨愚者執光向大義
衡陽新聞網訊 夜深人靜,青燈映照著殘卷《史記》,“君子不器”四字在紗窗上洇開微光。忽聞子夜鐘鳴,似遠古的回響,喚起我對華夏文明深沉的敬仰。歷史輪回,災難與光明交織而行,黑暗孕育光明,光明亦照耀黑暗。天地之間,總有一些“癡愚”者執炬逆行,他們被世俗視為“愚”,卻在生死中淬煉出永恒的光軌,讓大義在深淵里綻放如蓮。

▲燧光 徐瑞東攝
鐵血燧光
“你傻!”戰壕里少女的哭喊穿透硝煙,懷中少年喉間血沫滾動,卻含笑指向遠方:“那里……有光。”此情此景,令人動容,更令人深思。自古“男兒當以天下為己任。”正是這般“癡愚”,在逆境中將肉身化作那一抹不滅之光,點燃大義的火炬。
溯游歷史長河,無數“愚者”用生命詮釋何為大義。譚嗣同在菜市口飲刀時“我自橫刀向天笑”,徐錫麟被剖心仍高呼“軍歌應唱大刀環”,秋瑾斷頭臺佩劍刻下“休言女子非英物”,夏明翰就義絕唱“砍頭不要緊”,這些“愚者”實則是將血肉鍛為燧石的執光者。正如屈原抱石沉江,衣襟里落下的《天問》殘稿化作楚地磷火,淬煉中華魂;范仲淹戍邊詞里“濁酒一杯家萬里”的孤光,穿透兩宋陰霾;蘇軾夜游承天寺時,他的影子與“水中藻荇交橫”,寫出“何夜無月?何處無竹柏?”詩句,仿佛受傷的貝殼分泌出月光,凝成珍珠。黑暗無法吞噬光明,反而成為磨煉心性的砥石。

▲涅槃 徐瑞東攝
泥金涅槃
“金子埋在泥里,起初未必自知其價值。”卞和泣玉處,血浸璞石終化和氏璧;越王勾踐臥薪嘗膽,終成霸業;姜尚七十垂釣渭水,釣竿懸起八百年周祚;班超十年投筆從戎,終立西域之功;張謇在泥濘中奮起,推動民族工業的發展。“天生我材必有用”,泥中之金,經歷苦難的淬煉,終會發出璀璨的光。
“愚者”執光,不僅在古今,也在我們身邊。蘇武牧羊十九載,節旄落盡見本心;謝安潛心修養二十年,謝絕浮躁,終成一代名相;杜甫在亂世中堅持“安得廣廈千萬間”,用詩歌撫慰人心;錢學森歸國航程中默寫的《出塞》,比五個師的炮火更懾人心魄。誰又能說,這些“愚者”不是最清醒地活著?!實驗室里,白發教授第一百零二次推演公式,窗外霓虹閃爍,他心如磐。大義似金,總在至暗時刻顯其純度。

▲孤光 劉東華攝
孤光劈海
秦淮河畔,歌女撥動琵琶,弦音中藏著《玉樹后庭花》的亡國之音。而同一輪月亮,卻照耀著西南聯大的師生們,他們在炮彈坑邊點著煤油燈,課本里夾著聞一多未干的血跡。最暗時刻,總有人揣緊大義火種,執拗燃燒。
寒山寺的鐘聲里,鑒真第六次東渡的帆影刺破海霧。黑暗最殘忍之處在于試圖熄滅他心中的光,但他“傻”到用黑暗作渡海的舟楫,在驚濤駭浪中將盛唐文明帶到遙遠的扶桑。陳寅恪雖盲,卻以口述完成巨著《柳如是別傳》。所謂“愚者”,實是看透生死后與天道的盟誓,只要心懷大義,即使雙目失明,也能點亮一片光明。

▲薪火 劉東華攝
薪火鑄魂
今人常抱怨世道澆漓,卻鮮有勇者點火。看那敦煌藏經洞中,無名畫工在油燈下勾勒飛天衣袂,顏料里摻著三危山的流沙與信仰;守窟人三十年如一日,在莫高窟巖壁種下永不凋零的蓮花。
“黑夜給了我黑色的眼睛,我卻用它尋找光明。”在這個紛繁復雜的時代,“癡愚”不是盲目的盲從,而是“為天地立心,為生民立命”的守義者。
“人生若只如初見,何事秋風悲畫扇。”在追光的旅途中,每個人都可以成為那束照亮世界的光。讓我們與光同塵,與時代共震,因為“雖千萬人,吾往矣”的執愚,方是穿透永恒的最鋒利之刃。
合上書卷時,東方既白。文天祥的丹心仍在伶仃洋燃燒,陸秀夫的魂靈猶伴崖山珊瑚生長,王夫之“六經責我開生面”的硯臺里沉淀著整條湘江的月光,林則徐虎門銷煙的火光映出“海納百川”的胸襟。這些“愚者”用生命印證:光明不在云端,而在泥濘中跋涉的腳印里;大義不在史冊,而在凡人拒絕屈膝的堅守中。
且看那新綻的桃李,哪株不曾歷盡苦寒?“莫愁前路無知己,天下誰人不識君。”因為每一個甘愿在黑暗里播種光明的人,本身就是不落的星辰。
這,或許就是“愚者”們用生命書寫的終極智慧。